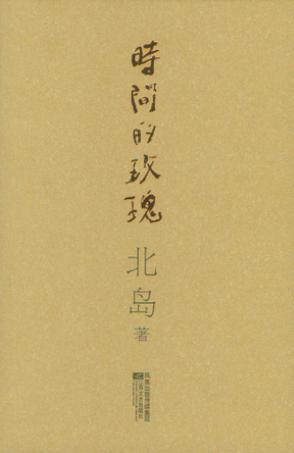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近几日只是乘得短暂的假期得以回家,出行前购得杂志《天南》创刊号一期,随编者所引进入的“亚细亚故乡”专栏又重新让我低下头俯身去审视脚边的泥土了。说起泥土,又回想起北岛一文《纽约变奏》里的场景——“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现在置身于繁华都市上层惴惴不安的一十二楼,走出阳台宛若漫步云端,却正如父母不经意提到家中再难寻桂花香了。
杂志打开了一个入口,让读者再一次观看脚下这片土地,以开篇对大坝的议题抛出一连串问号,忙不迭的追逼斥责着读者的良心。好在编辑的善良,不仅用日本和泰国的纪实找回了人与大地的联系,还描摹出了“中国乡村建设者的群像”,给人以希望。
当初在阅读阿兰达蒂·洛伊对印度政府和社会的对大坝的控诉之时,我正坐在高速驶回杭州的大巴上,公路两旁是长三角富庶的农村景象,较之当年巴黎境内的火车窗外的景象毫不逊色。但是我清楚车窗外的风物在百里千里之外便大相径庭,去年清明火车北上帝都之时便看着火车车窗外颜色由绿至黄绿最后逐渐一切都被蒙上一层厚重的土黄色。我没有进入过中国,一直在边缘的地方游走仿佛置身自己于高阁之上;我希望进入中国,走进一个更加真实的非加工过的“中国”。中国二字在我的脑中定义更偏向似黄土地上蒙着风尘的农人形象,一如”锄禾日当午“,中国的男子的形象;而江南,或整一南方疆域则大抵是中国女子形象的缩影。
印度和中国相似之处很多,文中所提大坝——我已记不得文中涉及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水坝,都无外乎让我联想到三峡,联想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文中的控诉通过这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不断的晃动三峡大坝在我脑中的固有形象:新闻联播中兴奋的播报员和那些只留下背影的背井离乡的农人;大坝合拢时欢呼的工程师和黯然叹息的文人学者。这样的形象塑造无疑将大坝本身置于级贬的位置,显然有失公允,毕竟,未来如何还未成定数。但由大坝所见的并非人类妄图改造大自然的傲慢,而是人类离弃其生长伊始的根基和牵系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小川绅介所言的“吃米的人”一说很是赞成。简单说来,“吃米”本身就告诉你你不是“流浪者”,这正是前些日子提到北岛在外漂泊自觉流浪若萍的原因吧。电视前端时候报道水稻杂交新的成果事宜,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袁隆平教授的意思,只是时常会为土地本身担心:这一亩一亩的土地到底能被人类挤榨出多少价值。也许只有这些不懂得科学的感性的读书人才会幻想出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国度,而真正愿意为之付诸于行动的那些乡建者才理应是我们这些抱怨牢骚满腹的所谓愤青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吧。
是的,那些只知发出怨艾国家、政党声音的年轻人自诩是高觉悟高文化的,却鲜有如梁鸿《行动在大地》一文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人的行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大学至今未能有一次完整支教经历当是让我深感遗憾的。走近产出生命的大地,走近离此泥土最近的孩子们的周围,切身提供教育的支援和帮助,这些都是支教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体悟;但不止于此,也许只有起码三个月抑或半年一年的与大地生活在一起的经历才能让你明白你所做的并不是施舍、奉献或付出,而仅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感恩和回报。乡建是要去扭转这个已略畸形的社会结构,重新在人们(无论是农人还是城市人)心中根植下大地的这个概念。我想这应该是乡建真正的目的所在。
之后的四边文章仅读了前两篇回忆类散文。后面的小说就真不符合口味。这样的文艺类杂志在市面上愈来愈多了,倒也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