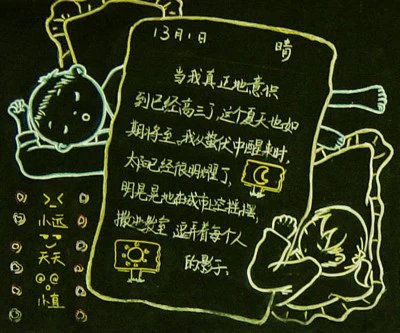却依然是这场冷雨
却依然是这场冷雨,下了许久许久的冷雨。不觉的,却又是自然的,我忆起去年的雨了。秋分一过,便是寒露。那种迷蒙的雨似是也笼了好些日子的。暮色已过,而寒意四起,只记得路灯洒落的红晕晕的光,全部融化到细碎的雨丝中,辨不清轮廓而宛如升腾的云雾了。当初气温是已逐渐凉下来,便不再去东区闲荡,以至于脑海中不能很清晰浮现出往日的图景。没有我的问候,他们自然都是还好的吧。白露未曾细见,已入严冬——没有雪而徒剩北风呼啸的冬。日子熬过去,熬过去,像是在小巷口煤饼炉上炖着小米粥,我穿着厚厚棉袄蹲着,看着一个个沸腾的气泡从黄而粘稠中缓缓一个个冒出来,然后又噗的破裂开,回复起初的平静,而后又是一个。全然不像那些吹出来的肥皂泡,动人的美丽之后,嗖的一瞬便消失在视野里了。 似乎寒假是能够养人的,春节过去,又是南国的游历,生活的虚空之中便也填补不少。想着早春吧,似乎是应该见影子了,却又在忽的温暖之后落下阵阵冷雨。“东风解冻,则散而为雨“,却为什么寻觅不得东风的影子呢。又是夜晚,又是走过那些不怎么滑腻的路,灯光没有秋时的迷惘了,淅沥沥的雨中看着还是有着一份独特的纯净的感觉,那个时候,一如常噎在喉的旧事,即便没有全然吞入,至少有着顺畅而均匀的呼吸。却真的未曾想到,雨竟是下了如此之久,都以为近段时间平复的心续,却在淋着、浴着、承受着一场场春雨后,将水一并从眼眶中倾流而出了。